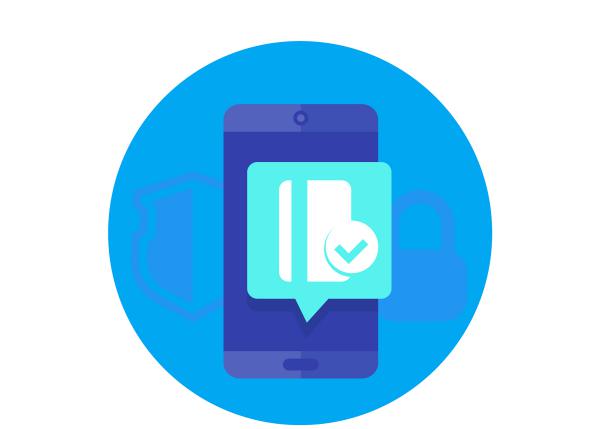我以为,我们的梦想已经失落在呼啸而过的路上;我以为,我们注定生存在一个根本不值得大师用文字记取的时代。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传媒人是从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里寻找到梦想的种子的。
19岁那年的一个春天早上,哈佛大学二年级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他开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26岁的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我是在十八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当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的时候,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所有生活在世纪转折的中国青年,几乎是一个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整整一代。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繁琐的职业、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物质的诱惑,为了让父母放心、伴侣幸福、上司满意,我们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预支、去交换。于是,有想象力者成了最优秀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有运作力的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再也没有人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总统”的面前。
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竟已经没有了一丝的不安和自怜,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代人的宿命,不管我们有没有了望到,它都将如期而至。
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的梦想已经失落在呼啸而过的路上,我以为,我们注定生存在一个根本不值得大师用文字记取的时代。
直到三、四年前,读到许知远和他们的文字。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青年人已经冲杀到中国最优秀商业媒体的核心,在一片血腥的故事和数据之中,这些充满了潮湿的梦想气质的喃喃自语一缕一缕地从水泥深处渗将出来,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是否喜欢了,它们依然象蚕丝一般地坚强,它们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李普曼、亨利?卢斯、托克维尔、罗尔斯、加尔布雷斯,这些名字像咒语一般地富有魔力,让一个平庸、浅薄而让人不耐的商业世界平添了一份怪异的精英气质。
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到来,让中国青年得以在一夜之间绕开所有的传统和包袱。当许知远们飞越重洋,敲开《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总编的办公室的时候,世界似乎真的缩成了一个小小的桃核。这是一些足以让所有人产生幻觉的对话和经验,它让我们相信改变是可能的,梦想是真实的,未来是真的会到来的。
此时此刻,当我一页一页地阅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年前的那个夜晚,月亮又大又亮,照耀在即将出发的道路上。我仿佛看到那个似乎沉沦的梦想又如泡沫一样地复活。
那个梦想,一百多年前,在刘鹗的书桌前曾奄奄一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无哭泣也,得乎?”
那个梦想,一百年前,在粱启超的海船上又曾复活了,“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那个梦想,从来是沉重和“不真实”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见美国的年轻人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她实实在在地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
做这两个世纪的中国人实在是很累。从粱启超、周树人到龙应台,再到我们,都是一些无从轻松的人,我们总是被一些无解的使命所追问,被一些没有着落的理想所驱赶。我们总是少数。当许知远在自己的blog上写到,“一份《新青年》比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纺织公司,更有影响力。”四周溅起的仍然会是一片嘈杂的不解和不屑声。我想这并没有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梦想是由所有人的肩膀一起来承担的。[!--empirenews.page--]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一些最终都到达不了目的地的人们――我甚至怀疑以“天生的全球化一代”自诩的许知远们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度上。
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总有一代人,会像李普曼那样地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等到《光荣与梦想》式的中文著作轰然诞生,等到《纽约时报》式的中文报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被响亮叫卖,等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国记者成为国家英雄。
然后,历史在他们手中“终结”。
然后,“最后的中国人”出现了,他们与龙应台看到过的美国青年一样,“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